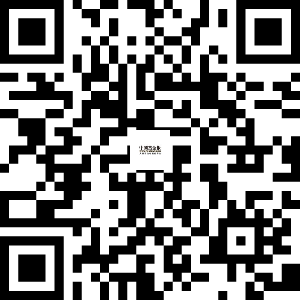吕锦明
就在上周五,备受市场关注的香港上市监管架构改革咨询结果终于揭晓,从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联合发布的情况看,为避免架空港交所审批新股权力的可能,最受争议的“上市监管委员会”将不会成立;同时,会在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之外成立新的“上市政策小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陈茂波认为,新安排能令上市政策及审批程序更加迅速和有效回应市场变化,对提升香港上市平台的竞争力以及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首选集资中心的地位非常有帮助。
就本次市场咨询,外界最关心的,其实还是港股市场是否需要以及何时引入“同股不同权”架构的问题。因为就在几年前,阿里巴巴原本计划赴香港上市,其“合伙人制度”实行的是“同股不同权”架构,但这却触动了港股市场实行多年的“同股同权”的原则。20多年来,香港市场一直奉行的“同股同权”或者“一股一票”,香港《上市规则》都明文禁止、限制不同投票权架构,因此,香港证监会此前曾以“同股不同权”将危害香港市场声誉为由而拒绝采纳。
因保留“同股不同权”架构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阿里巴巴随后转向投奔美国市场做IPO。有外资投行人士扼腕叹息道,如果阿里巴巴等科技创新企业能来香港上市,那么港股市场的交易量将有望增加数十个百分点,而这对于交易所来说,交易量的增加意味着服务费的增加;对于全香港来说,还可能增加当地就业,与上市公司相关服务的各项配套工作都会在当地完成,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由此,也引发了香港市场各方对究竟要不要改变“同股同权”的底线,来迎合以“同股不同权”为架构的科技创新企业来港上市的大讨论。为此,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展开了多次市场咨询。港交所曾表示,设立创新板市场接纳“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将有助于香港吸引内地大型新经济企业来港上市,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市场的竞争时,可以争取更多的科技网络公司来港上市。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如果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公司不在香港发行股票,投资者在市场上投资不到新经济代表企业,在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转型的背景下,香港市场引领金融资源配置的地位可能会减弱;同时,高增长行业于香港市场占比偏低导致市场发展停滞不前,也可能会削弱香港对潜在发行人的吸引力。
目前,港股市场就是否接纳“同股不同权”的意见可谓壁垒分明:反对“同股不同权”的一方认为,“同股不同权”给了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多的自主权,管理层可以获得投资者的资金而只需要受到较少的监督,因此担心权力会被“滥用”;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管理层掌握公司控制权,可以避免公司被恶意并购,如果控股权掌握在创始股东手里,可以规划长远的投资行为和发展目标,避免单纯追求短期市值而急功近利的行为。
其实,对香港市场而言, “同股不同权”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同股不同权”的AB股架构就曾在香港股市风行一时。究其原因,是当时的英资财团为了对抗来自日渐崛起壮大的华资财团的收购兼并,及保留自身的控股优势,于是采取了发行一些投票权与原来股票(即A股)相同、但面值不同的B股。但是,后来因为市场对此举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并引发包括华资财团在内的市场各方不满,数年后,当时的香港联交所及港英政府证监处决定叫停B股上市,并在1989年正式废除AB股架构。随着大部分公司的B股陆续被私有化,现在在港股市场上只有太古仍保留了AB股。
就香港市场目前的情况及长远的发展来看,引入“同股不同权”、吸引更多代表新经济的科技创新企业来港上市,并借此提高港股市场竞争力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似乎势在必行;但回顾港股发展历史可见,市场对于公平性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为此,有业内人士提出,在“同股不同权”公司达到一定时限后,比如:在上市后5至10年后,就需要就公司架构进行检讨是否需要转为“同股同权”,甚至解散合伙人制;同时,在发起人持股超过或跌至某一门槛,例如:持股超过50%或持股少于5%,监管机构便可以要求其转为“同股同权”;尤其是在持股比例跌至低点时,更要规范此类公司创办人等股东不能够将股份转售第三方。还有机构建议,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除了对此类公司加入“日落条款”,还要严格控制即将设立的创新板暂时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对此类企业的监管,应当与一般上市公司有别;另外,还要加强投资者教育,使其明确投资于“同股不同权”企业的风险等。
港交所目前的方案建议用两个方法对股权架构进行披露:一是规定公司要明确披露其不同投票权架构及与此有关的风险,此外也可能要求相关公司披露不同投票权持有人的身份。另一个方法是在披露规定外,对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实施强制保障要求,根据公司在创新主板还是在创新初板上市提出不同要求。
由此看来,港股市场要进行变革,监管方还需谨慎行事,广泛听取市场声音,从保护投资者权益出发,体现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